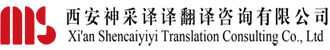语言与信息联通世界
探寻中国译学话语的发展之路——写在《中国译学大辞典》(第二版) 出版之前
发布日期:2024-09-02浏览次数:0
探寻中国译学话语的发展之路——写在《中国译学大辞典》(第二版) 出版之前
方梦之, 上海大学,上海200444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Written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Second Edition)
Fang Mengzhi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一部术语史就是一部专业话语的历史。术语是专业话语的基本要素,术语系统的建设是反映相关学科进步和走向的一面镜子。本文概述了《中国译学大辞典》(第二版)的编纂思想,介绍了该辞典的编辑方针、收选原则和编辑实践,从中可以看出我国译学术语的积累与译学话语体系的完善是同步的。这部辞典见证了翻译学科酝酿—诞生—发展的过程。
关键词: 翻译研究; 译学术语; 译学话语; 中国译学大辞典
Abstract
A history of terminology is a history of professional discourse. Terminology is the basic element of professional discours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ystem for terminology is a mirror of the progress and direction of any discipline. This paper presents an outline of the ideas underlying the compilation of 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Second Edition), and introduces the editorial policy, the selection principles, and the editorial practice of the dictionary. It reveals that the amount of literature on Chinese translations occurs in tandem with improvements in the translation discourse system. The dictionary has witnessed the conception,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translation.
Key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ological terms;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Second Edition)
方梦之. 探寻中国译学话语的发展之路——写在《中国译学大辞典》(第二版) 出版之前[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4, 46(3): 3-14 DOI:10.12002/j.bisu.516
Fang Mengzhi.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Written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Second Edition)[J]. Journal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24, 46(3): 3-14 DOI:10.12002/j.bisu.516
译道漫漫,文脉悠悠,理融古今,义兼中西。从支谦到钱锺书,从西塞罗到霍姆斯,人类对翻译学科的探索从未间断。试图记录古今中外翻译义理的《中国译学大辞典》(初版)(以下简称“初版”)于2011年面世,距今已10年有余,而为初版收集材料、钩稽整理的准备阶段更是可以追溯到21世纪初。彼时,译学的基础概念工具主要来自西方,我国翻译学的学科地位刚刚确立,译学话语体系尚在酝酿之中。翻译研究由语言学转向到社会学转向,由文化转向到技术转向,变化频仍。面对纷繁复杂的范式更迭和交替,学者们总是忙不迭地加以套用,急于在研究中引进新的方法和视角,往往还未来得及作好面对前一种范式的理论准备,就迎来了下一个“转向”。20世纪末期,我国译学园地虽曾热闹一时,但总是充斥着西方话语的高调嚣呼。
2000年左右,我国译学完成了“与国际接轨”,大规模理论引进的时期结束,开始进入自主研究的独立学科阶段。我国译学发展不再以新术语的大量引进为表征,而是以学理的深化、内涵的丰富、范畴的拓展和译学话语的自创为特征(方梦之,2021:29-30)。“接轨”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在沿着国际译学轨道前行的同时,立足本土,创新理念,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译学话语体系,从我国大规模翻译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提炼新材料、建构新理论,为国际译学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初版顾问杨自俭(2004:3)先生曾告诫我们:“1. 从理论上搞清楚范畴、概念、术语的区别与关系;2. 按译学发展的不同时期梳理出译学的术语;3. 给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术语分类。”我国面广量大的翻译实践为翻译理论的提炼奠定了基础,为译学话语表达方式的创新铺平了道路。概念的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为满足我国译学研究之需,反映国内外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特别是国内学者的成果,我们启动了对初版的修订工作,编辑出版《中国译学大辞典》(第二版)(以下简称“第二版”)。
第二版的增订目标是:进一步整理迄今为止的译学思想,集古今中外译学术语之大成,特别是要呈现进入21世纪以来新诞生的术语,爬罗剔抉,传播我国学者的译学成就,借鉴西方译学思想,通过整合、转化和创新,提供专业性的基本概念和术语,以铸就具有国际影响力和中国特色的译学话语体系。
我们的任务是立足本土,建立具有解释力的本土概念体系,彰显中国价值,凸显中国智慧和中国思维。翻译学是经验科学,我国学者已经从传统译学实践和当代翻译研究中提炼出一批又一批的标识性概念,具有中国特色的译学话语体系正在逐步完善。译学辞典理应成为科学的、系统的、开放的话语体系的缩影。虽说辞典永远晚于现实,但阶段性的回溯、整理与建构必不可少。建构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创新理论概念和学术范畴。第二版将争取最大限度地记录译学前进的印记。
第二版力求名实相符,对得起《中国译学大辞典》这个令人敬畏的标题。为此,编者特别在“中国”和“大”两个方面下功夫:“中国”的题中之义是要体现辞典的中国特色,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和学术话语上力求反映我国译学研究的传统脉络和当下水平,做到科学化、精细化;“大”则指范围广、规模大,是博大和浩大。译学所系学科交叉,学理纵横,翻译本来就被吕叔湘先生称为“杂学”。大辞典的任务是细大不捐,应收尽收,在繁杂中理头绪,在深邃中寻简约,提要钩玄,刮垢磨光,至显而寓至微,至约而寓至博,反映译学发展的脉络,呈现濯古来新的面貌。古今译学研究,论者如云。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派林立,百家争鸣。进入21世纪以来,翻译业态、翻译手段日异月殊,新理踵出,新术语、新概念层出不穷。第二版旁搜远绍,加以条贯,犹或未尽,工程之大,自不待言。译学与其他现代学科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除语言学及其众多的分支学科外,第二版中单列的学科类词条不下三四十条,旁涉学科数以百计。“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有2800余个词条生息于第二版这棵大树上。第二版文献浩瀚,数以千计,短短数百字的词条释义,往往需要引经据典,涉文数篇;加上前言、目录、附录等各种副文本,整本辞典不“大”也难。
翻译研究涉及的学科众多,是跨学科、多学科甚或超学科的研究,与人文各科甚至理工科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译学辞典是存储、追溯、展示、使用译学术语的知识库,译学的思想流脉、范式更替、交互转向、概念甄别等都可由此一窥端倪。因此,这一知识库的总体结构设计,包括栏目选定、条目分布和词条撰写等,既要便于“按图索骥”,又要符合学科逻辑。第二版仍以笔者“一体三环”的译学发展时空图为结构框架,一一安排细节。“一体”即译学本体,是译学发展之本,千百年来不断壮大、不断完善。该部分共分为12类栏目,包括一般概念、传统译论、现代译论、翻译学、翻译标准、翻译批评、翻译主体、翻译方法、翻译策略、翻译技巧、翻译类别和口译等。“三环”分别是:①语言和语言学,这是译学发展的原初性、奠基性学科,包括语言、文体、修辞、词汇、词义、语法、语篇、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等,分为5类栏目;②译学发展的支持性、工具性学科,包括哲学、逻辑学、伦理学、思维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文学、美学、信息论和社会学等学科,分为5类栏目;③文化与技术,翻译研究具有延展性、复合性和技术性,“文化”单设1类栏目,网络、语料库、语言服务和翻译技术等共设2类栏目。除了上述各栏目之外,“翻译教学”“翻译史”“国外人物”和“国内历史人物”单列为1类栏目。因此,第二版栏目设置增增减减,共分为26类栏目,比初版少了1类。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在翻译研究上追求创造性和体系性,高举“(翻)译学”的旗帜,“××翻译学”或“翻译××学”之类的术语不断涌现。据笔者统计,即使不计“变译理论”“译者行为研究”等系统性论说,这类术语也已有70余种。第二版收录了其中为译界所熟悉的三四十种,如“翻译哲学”“翻译美学”“生态翻译学”“翻译伦理学”“翻译心理学”“描写翻译学”“翻译符号学”“文章翻译学”等。这些术语的理论来源主要有3个方面:①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论;②交叉学科;③引进后被本土化的翻译学,如社会翻译学、语料库翻译学等。由此,第二版中各色“翻译学”及其核心词条倍增,在分类编目中不得不把“翻译学”从初版的“现代译论”栏目中分离出来,单独编目,以便查检(此举纯粹是从编辑角度考虑,绝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分类)。类似地,之所以将“语言服务翻译技术”独立编目,是为了反映进入21世纪以来语言服务和翻译技术这两个方面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翻译研究中新的学术范畴。
词条的分类很难铢两悉称。许渊冲“美化之艺术”的系列词条收在栏目“传统译论”之下,这是因为许先生的译论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和儒家经典,具有独特的民族性。他从自己的翻译实践和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提炼概念。虽然他表述在当代,是针对当代的翻译问题而发,但这些表述具有显豁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其译论是传统译论流脉的延续和发展。同样,按译论流脉,潘文国的“文章翻译学”也可归入“传统译论”栏目。文章翻译学以中国传统的道器论为建构的出发点,以严复从文章学角度解释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为之道,以“译文三合义体气”为之器,在此基础上建构其元理论、基本理论、应用理论和翻译实践的4个层次(潘文国,2021)。不过,“翻译学”有专设栏目,文章翻译学自成体系,因此最终按门类归入栏目“翻译学”。虽未标称“学”但有独到之处的系统理论都被归入栏目“现当代译论”,如任东升的“国家翻译实践”、黄忠廉的“变译理论”、方梦之的“应用翻译研究”等。有的词条明显横跨两类,如“翻译技术教学”,既可编入“翻译教学”类,又可收在“翻译技术”类。针对这种情况,编者在相应词条上加注了“互参”的标识。
以传统文论或儒释道经典为基础的译学分支还有许多,除文章翻译学外,还有“和合翻译学”“儒家翻译学”“大易翻译学”等。虽然其中难免有昙花一现的,但总体而言,翻译学的“版图”在不断扩大。
第二版集诸家之成,补初版缺漏,订初版讹误,对初版词条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吸纳国内外的最新成果,润改初版词条逾半,重写部分词条,删减少数过时的词条。第二版尤其在新词新义上发力,从源头上寻觅并选收新术语。确定新增术语的途径包括:挖掘传统术语、提炼现代概念、借鉴国外范畴、完善已有表述以及补充翻译史实等,其中前4项为主要途径。第二版新增词条900余条,词条总数从原有的约1900条增至约2800条。本节将主要介绍第二版新增术语的具体做法。
1. 挖掘传统术语
第二版挖掘了一批佛经翻译术语,同时也增加了一批近现代译家对传统译论概念的表述。
(1)增补佛经翻译术语
初版所收录的佛经翻译术语有限,第二版补苴罅漏,增添了上百条传统术语,词条涉及人物、学理、方法等各个方面。在古代译论中,进一步挖掘诸如慧远(334—416)的“厥中论”、鸠摩罗什(约344—413)的“依实出华”等术语;列出佛经翻译的范畴词,如“味”“境”“化”“隔”“圆”“妙”“和”“真”“言”“修”等;增添了著名佛经翻译家,如“摄摩腾”(?—73)、“康僧会”(?—280)等。
(2)选收近现代译家用语
近代以来,有无数先辈和贤达投身翻译研究,以鲁迅、傅雷、钱锺书等为代表的翻译家都拥有各自特色鲜明的译学话语,在当时的语境中充分表述了其译学思想,提出了一大批重要概念和创新术语,奠定了今日译论之话语基础。我国传统文论是源头,新范畴、新概念则是内容。对此,第二版特别注意吸纳近现代各位大师的话语表述。例如,在鲁迅使用的术语中,除保留原有的“兼顾两面”等词条外,还增添了“宁信而不顺”“拿来主义”“易解”“硬译”等。又如,钱锺书使用的术语,除“化境”之外,又补充了“虚函数意”“转胎投世”“不隔”“讹”等词条。此外,叶君健的“精品论”、曾虚白的“感应论”、郭沫若的“风韵译”、杨宪益的“历史距离论”等论说也一应收录。
2. 提炼现代概念
创新的术语是表述新概念的有力工具,网罗新术语、描述新范畴是第二版的主要任务,在这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
(1)网罗新术语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译界在翻译实践中不断创造新概念、新表述和新范畴。例如,任东升提出了“国家翻译实践”的新范畴,即主权国家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利的战略目标而自发实施的自主性输出和输入翻译实践(任东升、高玉霞,2015);汪榕培在翻译中践行了他的“传神达意”理论,即把形似和神似完美地结合起来——“传神”即传达原作精神,“达意”即传达字词和比喻的表面意义与深层意义;“阐释关键词”是我国对外传播的策略之一,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外文局的《中国关键词——权威解读当代中国》亮相两会新闻中心,以多语种方式向国际社会阐释和解读中国,受到国外记者的好评。这3个词条均被收入第二版中。此外,第二版扩大了翻译标准的概念范畴,除信达雅等学术标准外,还收录了语言服务中的各种实际标准和规范,如《翻译服务规范 第2部分:口译》《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翻译服务 第1部分:笔译服务要求》《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等。
(2)描述新范畴
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翻译学、变译论、应用翻译研究、译者行为批评论、文章翻译学等理论先后发展起来,它们自成体系,拥有自主创新的译学范畴。第二版约请上述译论的创导者们,分别从各自的理论体系中萃取精华,组成系列核心词条,概述各自的理论要旨。
许渊冲寿享期颐,一生笔耕不辍,尤擅诗词翻译,号称“诗译英法唯一人”。他实践与理论并重,根植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创造性地提出了“美化之艺术”的经典译论。初版仅收录了他的“三似”“三美”,第二版增补了“三化论”“三之论”“发挥译语优势”“创优竞赛论”“创译论”等概念。至此,许渊冲译学方面的系列主张和系统思想已得到全面反映。
与此同时,众多以“××翻译学”或“翻译××学”命名的创新学说带来了一批传统文论范畴、他学科范畴或与这些创新学说相结合的新范畴,衍生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对此,第二版选择性地记录在案。这类词条数目之多,让我们不得不把“翻译学”从原“现代译论”中分离出来,另立栏目,以平衡辞典结构,合理安排词条。
3. 借鉴国外范畴
大规模引进的阶段虽已成为过去,但是吸收和借鉴西方理论,为我所用,仍然是建构我国译学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
(1)直接“拿来”
部分概念及其表述可以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并对其来源和内涵进行解说(如例1—3所示)。
例1
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ology),由西班牙翻译家马丁(R. Martin)在2010年的《范式与翻译学》(“On Paradigms and Cognitive Translatology”)一文中首次提出,标志着该学科有了雏形,学科概念直接翻译而来。
例2
云翻译(cloud translation),指通过云计算技术提供的在线翻译服务。它利用云端的强大计算能力和人工智能算法,能够将输入的文本或语音内容进行实时翻译,并输出目标语言的翻译结果。该服务通常基于机器翻译技术,这些翻译技术通过大规模的数据训练,可以在多种语言之间进行自动翻译,提供实时、准确的结果。
例3
数字化翻译(digitalizing translation),指以数字化文本为基础的翻译。
其他术语,如“离散”“离散作者”“离散译者”“超媒体”“超文本”“无作者文本”“翻译职业伦理”“翻译技术伦理”“区块链技术”“大语言模型”等,在此不一一细述。
(2)“拿来”+发展
引进是为了发展,结合大规模翻译实践,我国学者对国外已有概念进行了完善。例如,阿皮亚提出了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的概念(Appiah,1993:817)。事实上,深度翻译是一种常见的翻译策略,我国翻译家严复早已在翻译实践中付诸实施。在严复的译作《天演论》中,按语占了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可算作我国翻译史上典型的“深度翻译”。曹明伦(2014)丰富和发展了“深度翻译”,将深度翻译分为显性深度翻译和隐性深度翻译两种。显性深度翻译是指译文中含有明显可见的解释性文字,有两种形式:置于文内,加上括号;置于文外,作为脚注或尾注出现。隐性深度翻译是指注释性文字与原文融为一体,一般以同位语、介词短语或从句的形式出现。对此,第二版均予以收录(如例4所示)。
例4
“(译者)主体性”(translator’s subjectivity)是20世纪末引进的外来词,与我国译学话语中早已存在的“(译者)主观能动性”同义。新世纪以降,译者主体性的话题逐渐升温,时至今日,未见消退,派生出“翻译主体”“翻译主体性”“翻译主体间性”等概念和术语。
4. 完善已有表述
(1)更新表述
概念的表述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学科的发展不断完善。第二版力图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例如,2000年前后“翻译产业”一词出现,多年后“语言服务业”兴起。2008年,我国学界开始使用“语言服务”一词,原来使用的“翻译产业”“翻译服务”逐渐少有人提及。目前,“翻译产业”已被“语言服务业”所包含和替代,翻译产业的内容已被整合到语言服务业之中。语言服务是翻译服务的扩展,“翻译产业”在概念上已成为“语言服务业”的下位词,如在中国翻译协会发布的《2018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中,翻译客户被称为“语言服务需求方”,翻译人员或机构被称为“语言服务提供方”。“语言服务”出现至今不过10余年,其概念表述本身也在不断完善。
(2)填平补齐
在学术研究中常见一些成对词或三四个内涵相关的成组词,如“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欠额翻译”与“超额翻译”、“逆向翻译”与“顺向翻译”、“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等。成对词或成组词收录的完备与否,往往是衡量辞典质量的要素之一。在这一方面,初版有所不足,如初版中有“结构主义”而无“后结构主义”,有“格义”而无“反向格义”,有“文本中心论”而无与之相对的“译文中心论”和“译者中心论”,有“旧译”而无“古译”“新译”。对此,第二版尽可能做到填平补齐。
(3)充实次级概念
学科的推进可以反映在重要范畴下次级概念的生长方面,研究的问题越深入,也就越接近问题的核心和真谛。例如,初版收有“回译”,近一二十年来对回译的研究多有进展,学者们创造了“无本回译”(textless back translation)、“文化回译”(cultural back translation)等术语,皆为第二版所收录。又如,初版中只有“文化转向”1个词条与“转向”相关,而第二版则增添了“语言学转向”“修辞转向”“生态转向”“社会学转向”“技术转向”等次级词条,使“转向”和“多重转向”的概念趋于完整。
在有关学科或范畴下补充核心概念可以帮助读者了解该学科与翻译研究的联系,如第二版便在“社会翻译学”词条下增设了“文化资本”“场域”“惯习”“行动者网络理论”等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5. 补充翻译史实
我国翻译史研究历来重文学翻译、轻科学翻译,若要进一步深化翻译史研究,就必须重视补充对我国近现代社会进步、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翻译家,挖掘翻译史上被忽略、被遮蔽的重要史实,实现由文学翻译史向思想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转向(方梦之、庄智象,2016:1)。为此,第二版收录了一批在社会科学和理工翻译方面对学科的引进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专家兼翻译家,他们自身专业成就的辉煌往往掩盖了其对翻译事业的贡献,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潘光旦,心理学家高觉敷、唐钺,地质学家丁文江、张资平,语言学家高名凯,经济学家杨敬年,政治经济学家李达、郭大力,哲学和宗教学家贺麟、吕振中、吴经熊,数学家郑太朴,医学家丁福保,地理交通学家冯承钧,等等。此外,第二版还收录了在对外传播或外事方面成就卓著的师哲、吴亮平、沈苏儒、段连城、冀朝铸等人,他们既是各自领域的专家,同时也是成就卓著的翻译家。不仅如此,第二版也收录了近年离世、还未来得及纳入翻译史的翻译家,如杨自俭、王宏印、汪榕培、谢天振、许渊冲、张培基、张佩瑶、邓正来等人。除酌量增补历史人物之外,第二版也充实了佛经翻译和近现代部分翻译史料。
从古至今,翻译载体经历了口头文化—笔录抄写文化—制版印刷文化—数字信息文化的更替,第二版在翻译史部分对上述各阶段也略有增补。
第二版的重点之一在于反映21世纪初期我国译学研究的发展状况。在这一历史时期,我国的翻译研究站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开始确立,用中国理论来解释中国翻译现象已成为日常,具有继承性、时代性、原创性、自主性的系统理论不断产生。表1列举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6种学说(以诸论问世的时间先后为序)。倡导者们提出了一批新范畴、新概念、新术语,其核心概念均被第二版一一收选。可喜的是,这6种创新理论的首创者均欣然应邀,以刻炼之笔为第二版的系列词条书写各自的理论精髓。
表1 21世纪初期我国译学研究最具代表性的6种学说
名称 | 首创者 | 首创年 | 第二版所收核心词条举例 | 代表作品 |
变译论 | 黄忠廉 | 2000 | 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等 | 《变译理论》,2002 |
生态翻译学 | 胡庚申 | 2001 | 文本生态、生态翻译环境、关联序列、译有所为、翻译即生态平衡等 | 《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2013 |
应用翻译研究 | 方梦之 | 2003 | 一体三环、学科架构、分层研究、中观策略、微观技巧的理据、应用翻译三原则等 | 《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与技巧》,2013/2019 |
文章翻译学 | 潘文国 | 2008 | 传统资源、道、器、译文三合、古籍英译的起始性原则等 | 《中籍英译通论》,2021 |
译者行为批评 | 周领顺 | 2010 | 译者行为、译者行为准则、译者行为批评模型、译者行为社会化、译者行为度 |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2014 |
国家翻译实践 | 任东升 | 2015 | 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能力、机构翻译、制度化翻译、翻译制度化等 | 《国家翻译实践初探》(《中国外语》2015年第3期) |
除上述词条作者之外,译学界其他专家学者也参与到修订工作中来:我国翻译界领军人物许钧教授和谭载喜教授分别撰写了基础核心词条“翻译”和“翻译学”;专攻翻译教学的文军教授及其博士生团队重新规划了“翻译教学”栏目,审订和增补了一系列词条;曾利沙教授补充了一批认知方向的词条;傅敬民教授提供了社会翻译学的基本术语;范武邱教授及其博士生王昱等整理了国内外翻译期刊的信息并补充了国外人物词条;许建忠教授书写了他自创的翻译学的条目;王华树教授审订并撰写了若干翻译技术方面的词条;熊宣东教授充实了佛经翻译的重要人物并审订了相关条目;易曾权副教授地毯式地搜索了海量的翻译研究书籍并汇编成目录……正是在以上教授和青年才俊的参与下,第二版才得以荟萃古今中外译论之精华,发百家之声,采众家之长。
初版的编委谭载喜、郭建中、王宏印、王克非、张美芳、陈宏薇、穆雷、曾利沙、贺显斌、贺爱军、佘协斌、易曾权等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他们撰写的词条在第二版中多有保留。第二版正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问世的。一字一句,当思作者心力;一词一条,恒念作者创造。
值此第二版即将面世之际,我们特别怀念曾为初版献计立言、删芜正讹、撰写词条的故友林煌天先生、杨自俭教授和王宏印教授。他们的学术思想、译学贡献和学者风范在我国译界广为传颂,第二版“国内历史人物”栏目已为他们各立条目。
辞典永远晚于现实。在我国译界理论自觉增强、创新意识勃发的当下,新理踵出,词条收不及收。尤其是近年出现的新论,方兴未艾,如“国家翻译实践”,“集描写性、解释性、建构性、对策性研究于一体,是一个跨越多学科的新领域……分支不少、论题众多,应用研究前景广阔”(高玉霞、任东升,2023:157)。学理纵横驰骋,而辞典的编纂是有时限的;况且,从新概念、新术语的出现到被认可,还有一个时间差。这为辞典工作者留下了补苴罅漏的空间。
翻译研究领域宽广,文献浩瀚,笔者蛰居一隅,见识有限。其中释义偏离、简繁失当、备证不足、考证疏舛、予夺不公等问题在所难免,仍需匡谬补正,深望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