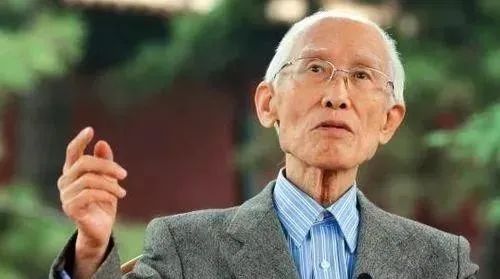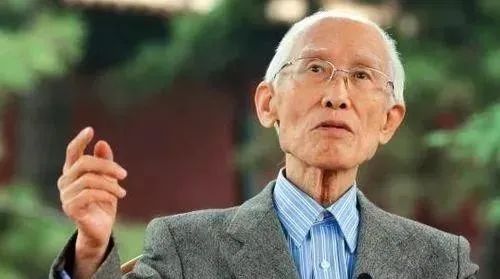
许多人都知道余光中先生是著名文学家,我们读过他的散文和诗歌;可是,很多人不知道,余光中先生还是一位翻译家,他翻译文学作品,也从事翻译教学。在1997年12月于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翻译教学研讨会上,余先生做了大会重点发言,同时也在各种场合谈论他对翻译问题的看法。他的讲话机智幽默,妙语连珠,常令人捧腹。笔者根据录音整理出余先生会上所有关于翻译的演讲,以便读者了解他的翻译观点。
翻译在中国古代就很发达。鸠摩罗什曾说,翻译是嚼余喂人。在座诸位都是“吃翻译饭”的,此话虽不高雅,但我们这碗饭吃得都很辛苦,一面自己吃,一面还要喂别人吃,即翻译教学,也是我今天要讨论的问题。翻译教学方法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从原理、从理论出发,应用到实例的演绎方式;二是从经验出发,把每一个实例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归纳出原理,这就是归纳法。翻译究竟是艺术还是科学,或是一种技巧?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如果原作有艺术价值,有系统,也许它是一门学科或科学。如果翻译作后面一种用法,则译员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如果把翻译作为一门艺术,译员就不是可以训练出来,而是修炼出来的,翻译教学的方式当然也就不同。科学与科技不一样,跟技术也不一样,我相信最伟大的科学家最富有想象力,他的某一阶段的成果不是靠推理得出来的。我有很多科学家兼文学家的朋友,都同意这个观点。我看过英美人编的一本书。有一部分专门是科学性质的文章(不是科学论文)写得美极了,可以称为文学,因此不能把科学与文学截然分开。我自己在读天文学的入门书时,感到宇宙之大,解放了自己的想象力,很想写诗。可见科学与文学不是截然相对的。美国女诗人米蕾(Edna St. Vincen Millay)写过一首14行诗,第一句就说:“只有欧几里德见过赤裸裸的美。"她把几何与艺术合为一体,毕加索就更进一步,根据塞尚的立体几何美学,发展了立体主义。因此我们不必把科学和艺术对立起来。例如徐霞客,他是地理学家,但又是散文家。我教翻译多年,一学期三学分。第一周讲概论,如翻译的功用、翻译的意境、翻译与创作的关系、翻译方法论、翻译史、翻译与文体的关系等。开列参考书目,让学生自己去追踪读书。笔译练习占主要成分,有6周。虽然我自己写文学作品,但我认为不应该开始就让学生研究纯文学翻译,因此开始6周的议题包括哲学、宗教、历史、社会和新闻等方面的东西,让学生各方面题材都试一下,然后4周进行纯文学翻译,如翻译诗歌、小说和散文片断,或文艺批评文章,或警句格言等。做教师非常辛苦。开始我采用的练习方式是,布置作业,改作业。后来改为:第一周把题目发给学生,第二周交卷,第三周改完发还学生,同时讲评。每个人单独详细改,讲评是综合全班的问题一起来讲评。佳译我会在讲评时举例,误译个别纠正,有隐恶扬善之意。第四周学生听完讲评后要再修改一遍,第五周我批改完再发回去,逼着学生详细看我为什么要改。如此反复两遍之后,译文就比较准确了。我上口译课用剧本让学生轮流扮演一个角色,一个人译,我从旁加以纠正,全班受益。戏剧有情节,对话又有趣,学生兴趣极高。每当两节课连上时就上笔译,单独一节就上口译。因为我觉得学生将来译小说会遇到对话,对话的翻译有自己的特点,要译得流畅,用讲话的方式。最后四周上汉译英,我一定让他们译一段古文,如韩愈的《杂说》,诗词各一篇,最后再译当代白话文。翻译课只有一学期。论文指导的情况,以我任教的高雄的中山大学为例,硕士论文可以翻译一本小说,一首诗,或者一个剧本,诸如此类,但译完之后要用英文写40页以上的评介,加起来要求比单写论文还要高。我指导过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的翻译。台湾近10年来设立“梁实秋文学翻译奖”,分为诗歌和散文两类,我一直参与出题和评审,每次还有另外两位评委。译诗组每次译两位诗人的作品。我们每次从早9点到晚7点,花一整天功夫进行评审,三人负责从头审到尾。我们评得很辛苦,“左顾右盼”,“望洋兴叹”。评完之后还要写评语,我也写了10年,每次1万字左右,不仅指出得失何在,还要加以修改,要示范,比较麻烦。我认为这属于广义的翻译教学,是社会教育。理想的翻译教师应有“三德”:一要有见解,包括理论水平、见识等;二要目光犀利,要眼光高;这两德属于学者。第三德属于作家,即手高。翻译教师仅仅"眼高手低"不算称职。手高包括了眼高,一个人不可能眼低而手高,手高也包括有见解。任何译作都是翻译理论不露声色的实践,所以只要手高就证明他眼高,也许他有自己的一套见解,也许没有写出来,但是一定会有。在前几年另一次翻译研讨会上,我提出一篇论文,题目叫“作者、学者、译者”。其中一段话说:“译者其实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没有创作的作家,即译者必定相当饱学,善于运用双语,其中一种应尽窥其妙,另一种要能运用自如”。理想的手高也应有“四德”:一是应个别、详细批改学生作业,不能粗枝大叶;二是应尽量保留学生原来的译文,因为"愚者千失,必有一得”学生的作业中总有一点可取之处。教师若彻底否定,学生会丧失学习兴趣,也没有自信了。因此我尽量保留能用的部分,实在太糟的再动手术,加以修改,保留得越多,学生越有自信;第三德是顺应学生译文的风格,这样才能鼓励他朝自己的方向发展,形成自己的风格;第四德应做一个称职的文体家,这个要求也许太高了,这是一个很高的理想,很难达到,不过不失为我们奋斗的境界和目标。翻译家一定是一个各种文体都拿得起的文体家。名师是否能出高徒?状元教师是否能带出状元徒弟?我们有了一套很好的理论,有了称职的教师,学生也必须具备起码的条件,他双语根底要厚。可是中英文俱佳者未必是一个好译者,未必掌握了两种语言就能使二者成为“佳偶”,也许会变成“怨偶”。理想的翻译,从译出语进入译入语,译文比起原文来,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孪生”,退而求其次,至少二者应像兄弟姐妹,再差一点至少是表兄弟,堂兄弟。如果搞到后来变成“远亲”或“同乡”,那就差得太远了。因此翻译能力除了双语功底外,还需要一种特别的调整适应能力,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协调各种关系。而社会环境给学生提供的往往是翻译的反教育,反教学。我们每年出许多译著,台湾的报纸上也有不少书评,可是这些书评很少评论译得怎样,只说其内容怎样高超,原作者怎么伟大,很少有人去鉴定翻译的质量。译书与写书一样,“尽信书可能不如无书”,不少译著不负责任,造成反教育。第二个反教育是一些著名作家学者写的文章西化,看起来是论文,其实是西化的语言,这是不良示范。另外在各种媒体上的广告对白和用语、英汉双解词典中的例句,不免会有反教育的作用。我的结论是:我们身为翻译教师,应时时自我反省,看看我们的笔下和口头,语言是否流畅、清新、自然、地道、优美,否则自己就会变成一个污染源,自己习于西化而不自知,误人子弟。翻译教师正如国文教师,广义上还包括广大的学者,对于维护中文的清新、自然、优美都有重责大任。因此,翻译是另一种“国防”,是一种防御措施。我希望大家,尤其是我自己,能够时时反省。在翻译教学研讨会上,中国译协的部分学者就翻译批评等问题请教余光中先生,下面是几位学者和余先生的对话。余:我虽然译了一些书,也教翻译课,不过我主要是个翻译实践者。我没有兴趣做翻译理论家,但我有兴趣做翻译批评者,去评别人的译作。我自己不准备提出一套有头有尾的完整的翻译理论,因为有许多学者已经写出这样的书,而且写得很好,如刘宓庆教授等。我觉得翻译理论要配合翻译批评、翻译书评或翻译某一题目的专论,泛论式的理论固然需要,但针对个别翻译的成就得失的评论即个案处理的评析也需要。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实践,学生要尽量多实践。我刚才在报告中指出,我在教学中分五次把一篇习题处理完,第二周又发第二篇习题,如此循环,学生一学期要做14篇习题。问:奈达在一篇文章中说:“Outstanding translators are born, not made.”即杰出的翻译家是天生的而非造就的,余先生对此观点怎么看?余:我刚才讲名师未必能出高徒,可是我也没有说名师未必不能出高徒。名师指点的那个徒,如果是可以点化的,可以造化的,名师可以帮助他成为高徒。至于说“Outstanding translators are born, not made”我不赞成。我刚才分析的是翻译教师,当然包括翻译家。我认为翻译家要有见解,要眼高,也要手高。眼高和有见解是修炼出来的,手高也许倒是有点天生的,因为手高牵涉到作家的写作素质。前面两"德"是学者之德,学者一定要自我锻炼,自我锤炼,绝对不是天生的,即使有天赋也需要修炼,有先天也要有后天,就连天才的作家也仍须自我修练。问:目前在大陆,搞文学翻译的人路子越走越窄,因为许多人对文学没有兴趣。不知港台是否也有这样的现象?余:我想也是有的。一般的书评只是介绍译作的内容而不评论其翻译的优劣。问:对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个问题,请问您的看法如何?余:我虽然是从事文学翻译的,可是我也承认,翻译有一部分是要给大众看的,他们不想看纯文学,他们看知识性的,如旅游的、教生活常识的,或者一些很实际的东西,这也需要大批称职的译者。不是说他们可以乱译,他们也应该译得很好,不过这跟文学翻译大不一样。从原则上说,一般的翻译好好训练可以达到,而文学翻译是需要修炼的。我自己赞成把翻译当作艺术来看待,我的一些朋友,包括语言学家,他们宁愿把翻译当作科学来看待,因为他们把语言学当作科学。文学家和语言学家往往会就此争论不休。问:什么样的人具有从事翻译批评的资格?从事翻译批评者本人是否一定要是翻译家?余:他本人不一定在做翻译。翻译评论者不一定要手高,他不见得在翻译上要有什么成就,但他要眼高,要有文学批评的修养。问:可否请您解释一下:有人说,如果自己没有译作的话,就没有资格进行翻译批评。余:有的人并不写诗,但他可以论诗,他只要是学者就可以了。问:持这种观点者认为,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可以分开,但翻译批评与翻译实践分不开……余:我觉得一个高明的学者不是绝对没有资格进行翻译批评的,主要看他评得是否在行。如果他眼高,眼光犀利,看得准,讲得又有道理,那有何不可呢?比如有人说,只有诗人才能译诗,那就太绝对了,翻译恐怕做不到这么绝对。问:现在的问题是,有译作的译者不肯轻易批评别人,因为别人会反过来批评他。问:如果说没有译作就没有资格进行翻译批评,有了译作又不便去批评别人,那么谁来进行翻译批评?怎样从逻辑上解释这个悖论?余:文学界也有这种现象:文学家去批评别人,别人也会来批评他,“门户大开”“我不犯人,人不犯我;我若犯人,人必犯我”这样就不能进步。当然要去批评别人,自己要“守紧门户”,自己翻译就要小心,否则惹了别人,别人也会向你挑战,“一报还一报"是可能的。大陆还好一点,从东北到云南,闹翻了就闹翻了;在台湾的话,从台北到高雄,你骂了他三天就又见面了,“短兵相接”。你们那个“飞弹”打了就打了。不过真正翻译要有评论的话,就得牺牲一点,翻译批评一展开,是非必然很多。但无论怎么是非多,还是要开展翻译批评。问:对,否则把翻译的批评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贵族化,学院气太浓,不利于翻译事业。应该鼓励翻译批评。余:对呀。翻译理论跟翻译实践之间有一个地带,即翻译批评,就是理论的应用,理论之实践。我刚才说,我有兴趣做翻译批评,因为翻译理论好比《孙子兵法》,是全面的理论,很重要,但怎样针对个案运用这个理论?写翻译评论好比领兵完成突袭的战役,很浪漫,很刺激,很有趣。问:像您这样的学者,既是学者,又是翻译家,从事翻译批评,别人心服口服,但……余:中间有模糊地带,不见得完全心服口服。有人喜文、有人喜白;有人简洁,有人详尽,这个弹性还是有限制的。很难说服气不服气。问:《中国翻译》对有些翻译批评文章就不敢登,怕闹得不可开交。余:本来我们讲"远交近攻",翻译批评其实可以"近交而远攻",我也做过这样的事。我和一些知心朋友为梁实秋翻译奖的译者做评审,写评语,十年过去了尚未引起纠纷。不过我们做此事非常小心,自己不能看走眼,要眼高,自己对原文要透彻了解,你说译者某处译错,还要动手帮他修改,就是也要手高。问:您写译评没有纠纷,大概有“李小龙”的意思,别人不敢跟您动手比试比试……余:我们也是很谨慎的,我讲你要有把握,不会错的,让你没有反驳的余地。问:文学界专门有人从事文艺批评,翻译界有无可能专门有人从事翻译批评?余:当然应该有。香港今年去世的一位学者宋淇,他就常写翻译评论。他读译作读得很仔细,每发必中。他自己翻译实践不太多,有相当翻译经验,不过他写译评比翻译实践做得多。问:可不可以有翻译批评家这个职业,专门有人从事翻译批评?余:可以呀,多出现几位这样的批评家,翻译界大家都会小心从事。翻译协会对粗制滥造的翻译现象应该有所制裁,否则这些劣货会排斥良货。问:翻译界有个别人"老虎屁股摸不得",你批评他,他能骂你个狗血喷头。余:这种现象台湾也有。台湾最近就有这样一件事:一位很有名气的作家兼教授,译了一本叶慈的诗选,错误不少。另一位翻译名家写了一篇书评,原译者就答辩,不接受意见。评者第二次再加以评论时被退稿,他一气之下把退稿登在一份杂志上,而且标题是《被某报拒登的书评》。这当然不容易,不过翻译批评的风气应该慢慢展开,否则读者也不知道译作是否可靠。问:余教授,您刚才提到生活在社会上,语言会被"污染"……余:我自己就被“染”过,所以才知道“染”字的危害。我大学毕业之后不久翻译了一部《梵高传》。过了十几年,出版社说这个译本已经绝版了,再修订一下重新出版吧。我花了一年功夫检查了一遍,600多页的这本书,我改了一万多处。有的朋友问:“你当年的英文这么差?"我说:“那倒也不是,我改英文错误的地方并不那么多。绝大部分是,我已经不满意自己十几年前使用中文的方式,我认为自己那时的中文没有自觉,有若干地方是不必要的西化。我一直在写作,慢慢就悟出来,我是读外文出身的,中文不知不觉地受外文影响。可是因为我自己写中文,读古典作品,慢慢就感觉到中文之道应该怎样,不该怎样。”问:我们读《红楼梦》、《水浒传》这类经典作品,是否就可以使自己的语言比较纯正? 余:对,除了读古典文学,还要读旧小说,只要是《老残游记》以前的东西,都不是西化的。问:余先生,您是否认为茅盾和巴金的作品受西方语言的影响?余:已经有影响了。当代的文学作家,也有一些语言比较纯正,不受西化影响的,比如沈从文的作品,他不懂外文,不受影响。也有少数作家可以让学生好好读。不过,我可以说,大多数作家靠不住,尤其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术语如林,很难避免西化的影响,什么都“化”了,如naturaliz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什么都“化”掉了。我觉得不能什么都机械地“化”。比如"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必须深化",其实"必须加深"就可以了;"你这方面太弱了,应该加强",不必"强化";要多想想中国是不是已经有这个说法。我不是说"性骚扰"一定要改,“性骚扰"也很有味道,很刺激,可是本来我们中文讲"调戏",这个词不但有语言,也有动作。另一方面,翻译作品难免多少带有一点异国风味,对刺激本国文学发展也有帮助,一概太"中国化"也是病。这就好比你带一批游客去游美国,却偏偏领他们去唐人街吃中餐,那你去美国干什么?不如直接去中国。所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洋味,但要斟酌,要有分寸。问:我们也有一个比喻:中国的作品好比一杯"茅台",西方作品好比一杯葡萄酒。把中文译成外文之后,它应该还原为一杯茅台酒呢,还是应该变为一杯葡萄酒?或者是带点葡萄酒味的茅台?抑或是带点茅台味的葡萄酒?余:这是一个大问题。茅台对中国人的味觉,相当于葡萄酒对西方人的味觉,不能把二者兑起来,也不能取代对方,这就比较复杂。如林文月翻译《源氏物语》,那是很大的成就,她送我一本。我不懂日文,说她:“略带‘和’气。"她听了很受刺激,想把译作修改得没有"和"气,不过完全没有"和"气又不大像了,这个很难掌握。有时候是蛮漂亮的"混血种"而已,"中西合璧"。如美国女人穿旗袍,另有一番婀娜爽健之风。翻译要取得"平衡"或"中庸"。我以前常觉得,译者是一种“媒婆”,两种语言如此不同,可它们能够相安无事,相得益彰,译者是很了不起的。后来我觉得这样做又像对待敌人,因为原作语言与译文不一样,译者要在其中取得平衡,好的译者应该能够“化敌为友”,至少暂时为友。我有时想这就像《三国演义》一样,孔明碰到鲁肃怎么办。他们小我之间是朋友,大我之间是敌人,可他们实际的关系是对手。鲁肃不如孔明聪明,太老实,每次都要吃点亏。两种语言间要化敌为友,要看译者哪方面比较强。他的中文强一些,原文理解就会差一点,反之亦然,这就像孔明鲁肃之间的关系,总是孔明占上风。如果能做到二者平衡,那是很不容易的。香港中文大学翻译学系系主任金圣华教授在大会上介绍了她对翻译教学的认识和体会,余光中先生在金教授发言之后评论道:金教授自己从事翻译实践,同时带17位学生的长篇习作,实在不易。我带一个学生尚勉强,好比赵子龙大战长坂坡,怀里抱着阿斗勉强尚可应战,而她要怀抱17个阿斗,还不滚下马来,这真不简单。钱钟书说过,做教师的改作文,好比开洗衣店。送进来的都是脏衣服,送出去的都是干净衣服。可下星期同样又是脏衣服送进来,永远不可开交。所以我们常说,父母把孩子"拉扯"大,学生长大,是老师把他"洗刷"大。金教授自己做翻译,又指导学生翻译,又要为香港的法律等文化事业出力,又要研究译学,又要主持译政,她对翻译的贡献真是很大。我想应该给她一个什么头衔。本应称她为Ms Translation,可念出来别人会听成mistranslation,变成“误译”,于是只好采取"修正主义",改为“Lady Translation”。来源:
穆雷.余光中谈翻译[J].中国翻译,1998,(04):38-42.